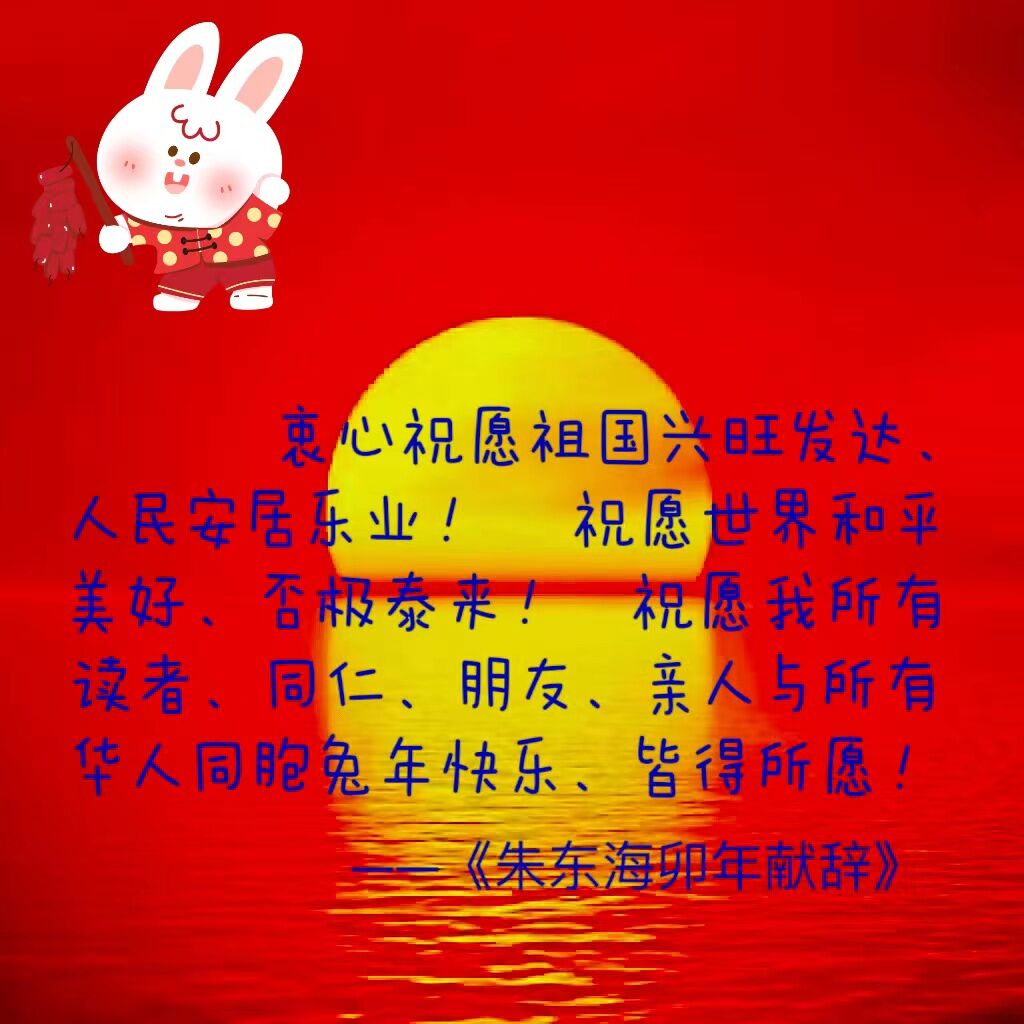林怀民:艺术影响一个国家的气质和走向-凯发k8网页登录

2011年4月,林怀民携“云门舞集”经典作品《流浪者之歌》巡演于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杭州、武汉六城。与巡演配合的,是一系列的讲座、采访和新书签售,慕“云门”之名而来的观者安静地享受着与林怀民的对话。
“林怀民”与他主创的“云门舞集”,已然成为一个文化符号,成为中华文化和台湾文化的重要部分。过去38年,云门舞集在世界舞台赢得赞誉无数,然而林怀民津津乐道的总是云门舞集的户外公演,在他看来,跳舞给基层的民众看,培养台湾民间优雅的品质,才是云门舞集最初和最终的理想。
常着一身黑衣的林怀民,从容不迫,温和谦恭,即使讲座上遭遇不礼貌的问题,亦淡然微笑着作答。他谈舞蹈、艺术、社会和未来,一下子就深入人的内心。
人的内心需要这些东西
《南风窗》:您在多个场合说过,如果只能留下一部作品,您希望是《流浪者之歌》,这部作品有什么特别的存在意义?
林怀民:它给观众一个安静、安宁的空间。这种空间,不仅现在的人们需要,到了22世纪、23世纪,人们依然需要。
对于云门舞集来说,这是一个转折点。从这部作品开始,舞者不再仅仅专注于表面的技巧,而更加关注身体和吐纳,因此近年的作品更多地融入静坐、太极、拳术和书法等元素。
《南风窗》:在《流浪者之歌》中,一个扮演僧人的演员在台上站了90分钟,黄色的稻谷细泻到他的头顶。整部作品都带有这种宗教的宁静,超脱于浮躁的社会。您会担心作品离社会太远吗?
林怀民:这部作品在大城市也在台湾南部的乡下,在台湾、大陆也在海外上演,无论在哪里,都没有改变任何元素,但无论城市的艺术家还是农村的大娘,都同样看得很专注。人的内心是需要这些东西的。
《南风窗》:云门舞集创办于1973年,在1988年曾经暂停。您说过暂停云门舞集,是因为看到社会一些很浮躁的东西,云门舞集彻底不能与世界对话了。后来选择回归,是找到了重新与社会对话的方式吗?云门舞集变了还是台湾变了?
林怀民:1991年我回到台北,回来的第二天,在计程车上司机突然跟我说话,“林先生,你为什么停掉云门舞集?”我讲述云门舞集经营遇到的种种困难。他表示理解,过了一会又说,林先生,每个行业都有艰辛的一面,我们开车子跑台北,生活也不容易。我下车以后,他摇下玻璃窗,伸出头来,朝我大声喊:林先生,加油!那时我感觉非常惭愧。在那一个月中,很多朋友对我说,云门舞集不可以停掉,有的以训话的语气,有的以规劝的口吻。我慢慢意识到,对于这些基层的朋友来说,云门舞集可能是他们生活的重要意义。我决定重新开始。我们不再那么在意成败,只是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。
《南风窗》:云门舞集创办之初,就被赋予了一种社会责任感吗?
林怀民:如果只是为了满足创作或生活需要,我可以写小说,或者去大学教书。但那时我25岁,刚从美国回到台北,心里充满着改变社会的渴望。如果某个环保团体需要我,我也会毫无犹豫地投身。只是恰好遇上了一批舞者和音乐家,大家心里都涌动着想做点什么的渴望,这点什么后来变成了云门舞集。创建云门舞集,最初是基于这种改善社会的愿望,因此从一开始,云门舞集的发展方向和经营方式就不同于传统的舞团,除了主团,还有二团,是专门到社区、学校和乡下演出的。
《南风窗》:作为一个民间舞团,云门舞集本身也面临很多困难,赋予它这种社会责任感会否过于沉重了?
林怀民:基层的演出虽然比较麻烦,但从中获得的鼓励是巨大的。你想象一下,民众把家里的电脑电视关掉,坐着公车骑着摩托车,大老远地来看演出,在地上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。有一次下大雨,也没有人离开,几万人披着雨衣坐在水里看。演出结束后,全部人鼓掌,给我们,也给自己。这是一种很舒服的对话。
很多舞者喜欢通过跳舞与基层民众交流。这是一种态度,没有什么沉重不沉重的。真正的压力在于在基层演出必须有好的作品,把观众吸引得目不转睛,才能维持现场良好的秩序,如果作品不好,观众站起来就走了。所以最后还是要回归到作品本身,即你有没有一部好作品。
最好的作品创作于解严之后
《南风窗》:云门舞集创办于1973年,经历了台湾的戒严和解严,这个转折对云门舞集的艺术创作有什么影响吗?
林怀民:相比文学、戏剧、流行音乐等,舞蹈艺术受到的压力相对较小,有关方面不会强迫舞蹈创作完全围绕政治。在戒严时期,我并没有清楚地感觉到不自由,而是解严之后,忽然觉得个子变高了。回过头仔细想想,并不是自己个子矮,而是戒严时期的天花板太低。
《南风窗》:空间感不一样了?
林怀民:戒严时期的禁忌并非成文的规定,而是一种漂浮于空气中的东西。除非你被抓起来了,否则不会有太大感觉。在解严之后,我才慢慢发现想象力可以无限深远,可以创作一些不同以往的东西了。简单来说,就是舞者不再服务于一些特定的文字或角色,白蛇和黛玉不一定要有青蛇和宝玉了。思想自由以后,舞者的身体和动作也获得了自由,在台上如鱼得水。我们最好的作品都创作于解严之后。
《南风窗》:所以说艺术与政治之间存在微妙的联系?
林怀民:一点都不微妙,而是很严重的关系。戒严时期有审查制度,一些作品无法发表,也有人被审查被起诉被关押,这是很可怕的事。但更可怕的是自我审查,在审查制度营造的氛围中,自己把自己憋起来都不知道,形成一堵无形的墙。解严后,墙倒了,露出了遥远的蓝天,想象力可以尽情驰骋。这反倒是另一种考验,即你要证明自己有想象力,而且有能力去呈现自己的想象力。但我绝对不愿意回到任何有审查制度的社会去创作。
《南风窗》:很多民间舞团不可避免地面临资金困境,云门舞集似乎做得比较好,现在已慢慢走向了财政稳健,是怎么做到的?
林怀民:云门舞集几乎每场表演都满座,但还是缺钱,很多人对此不理解。舞蹈演出不同于流行音乐,流行音乐录一首歌就可以无限复制,但舞蹈演出的第1场和第100场,消耗的人力物力是一样的。全世界的这一类团体都难以自负盈亏,要依靠国家拨款、民间捐助和企业赞助来维持。
虽然我们仍不富足,但已经过了不知道明天的钱在哪里的阶段。企业界的支持是云门舞集活下去的重要支柱,比如云门舞集的户外公演是由台湾国泰金融集团资助的,至今第15年了。如果纯粹为了商业回报,它不会做这样的事。它更多是为了一个承诺,一个理想。15年的户外公演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和改变,并非物质可以衡量的。
2008年云门舞集排练场失火,所有东西付之一炬。在短短的3个月内,云门舞集收到5000多笔捐款,有企业的两三百万,也有小朋友寄来的100元。我们走在路上,经常会有人跟我们说“加油”!没有企业和民众的支持,云门舞集很难坚持这么长的时间,也很难在国际上走到今天的高度。
《南风窗》:您想到有这么多人捐款吗?
林怀民:没有想到,但我想所有的捐款都是为了一个期待,大家希望共同来完成它。我们租了一块漂亮的地重建排练场地,租期是50年。在重建计划中,新的排练场不仅供舞者训练,也对外开放,成为一个平台,一个旅游点,可以举办艺术节、儿童课外教学等。现在人们的娱乐活动只剩下卡拉ok和party,这不是一件好事。你用什么样的东西、什么样的态度去与人们对话,他们就受什么样的影响。我们希望可以培养出台湾民间优雅的品质。50年后,或许我已经不在这里了,但这些经由时间沉淀下来的品质不会轻易散掉。
《南风窗》:您说过,美国有一个公式,对于民间艺术团体,政府补助33.3%,民间资助33.3%,演出收入33.3%,是最健康合理的状态。现在云门舞集得到的政府补助只占15%左右,这一块是不是太少了?
林怀民:台湾对艺术给予全部的自由,这是最大的支持。补助的预算确实不理想,因为有关部门往往注重硬件的、看得见的投入,忽视一些软件的、看不见的东西。但是软件往往比硬件更重要。艺术需要长期的承诺,而不是一付出马上要求得到回报。
艺术永远可以安慰和鼓舞人
《南风窗》: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在推动建设文化产业园,这是政府支持艺术的一种好的形式吗?
林怀民:文化产业不一定是文化,这里面有很大的空间,完全看戏怎么唱。有些人不讲“文化”,只关心“产业”,最后把文化产业园弄得与艺术完全无关。
支持艺术有很多种方式。在台湾,企业家提供资助,请我们到他的家乡演出,这样既可以为家乡做点事,也在无形中支持了一个团体。在澳洲,有一个基金会专门购买年轻画家的作品,出租给市民,年轻画家既卖了画,基金会也得到回报。在巴黎,艺术家和学生们非常幸福,他们虽然很穷,但艺术的大门随时敞开着,去艺术馆看展览可以免费,听音乐会可以打折。现在大陆的美术馆和博物馆正慢慢免费开放,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。可是艺术展览和演出的票价非常贵,以我的收入都感觉难以支付,自然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被拦在剧院之外了,我觉得很心疼。
《南风窗》:艺术变成了一种非常小众的东西。
林怀民:年轻人需要这些东西。如果没有人给他提供精神上的粮食,他永远只会去买楼炒股。在德国,大剧院卖出的每一张票都包含政府补贴,所以票价不会很高。中国大城市都建起了豪华的大剧院,节目也越来越多,但票价太高,人们进不来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,剧场本来是为了让人们进来,尤其是让年轻人进来的,他们代表着未来。
《南风窗》:您是说政府支持艺术,不仅要投入资金,还要投对方向?
林怀民:是的。盖大楼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,几年之内城市就能换个样子,但社会气质的改变和个人素养的提高,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多方面的汇合,并非学校集中集训就可以完成的。二战时期美军轰炸德国最激烈的时候,德国还有地下音乐演出。人们聚集到地下室,用黑布把所有的窗户都遮起来,在里面安静地听演奏。当时人们饿得皮包骨,但听完音乐会,走出地下室,感觉还能活下去。德国战后复建之快没有令我感到很惊讶,因为它的文化中本来存在这种东西。日本也是这样的民族,日本人震后表现出来的从容镇定令人震惊。艺术不仅仅是感官感受,它还蕴含着思维和文化,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气质和走向。
《南风窗》:但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,流行文化却往往比纯粹的深度的文化更容易占据市场,这与发展阶段有关吗?
林怀民:这在全世界都一样,无关发展阶段。在纽约,人们在林肯中心看演出时很放松很快乐,但一走出剧场,说话的声音都变小了,面对着冷冷的地铁感到害怕,因为社会治安不好。如果刚才说的那些事情不做,社会可能变得更加离奇。而这对于大陆尤其重要。大陆地广人多,人们很难聚集在一起,但至少一起走入剧场一起笑一起哭一起感动的时候,人们是在一起的,而且是自己买票而不是被动员来的。
《南风窗》:您说过大陆是一个变数,这是担心商业对艺术的侵袭吗?
林怀民:商业的东西要发展,纯粹的艺术也要扶持,在五光十色之外要有一些安静的东西,才能形成一种对抗和平衡。在大陆,不要说剧场,连电影都遭受了巨大冲击。我非常怀念《秋菊打官司》时代的张艺谋。
当然,文化的培育需要时间,但很多东西不能等待,而这些东西会影响社会每一个人的价值取向。我有一个人类无法实现的梦想:实现精神的均富。我希望有一天,一个工地上的工人也能听着贝多芬,在那一刻把所有的委屈都洗刷掉。在西方,很多人并不富裕,也会花钱去看演出,当然票价不会很高,但从中得到精神的满足。这并不是很难实现,更重要的是培养起一种内在的价值观。艺术永远是可以安慰和鼓舞人的,不需要理由。
《南风窗》:您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让云门舞集走得更远吗?
林怀民:我不是一个伟大的舞者,从来没参加过专业舞团,傻里傻气地走到现在,只能说我很感恩,在38年后依然做着自己喜欢的事。我的理想没有变质,还是与出发时一样。我所做的一切,都是以云门舞集为桥梁去实现那个无法到达的梦想。(陈统奎)